 2021-08-30 |
2021-08-30 |  1376次
1376次 
提到武装冲突,人们总会想起冲突方在对方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场景。的确,从古至今,这些暴行一直是武装冲突的写照,但是冲突中经常发生的性暴力有时会被忽视和遗忘,更谈不上受到惩罚,这在21世纪的今天依旧如此。
所幸的是,联合国在2009年根据安理会第1888号决议设立了一个由一位高级代表领导的办公室,专门负责收集有关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情况,促进开展预防、支持受害者和追究肇事者责任的工作。
现任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腾来自南亚,她的家庭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父亲来自印度,外祖父来自新加坡,外祖母则是斯里兰卡人。外祖母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总是跟年幼的帕腾说,天空有多高,你就能飞多高。而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父亲。
帕腾:“我1958年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国家——毛里求斯,那是印度洋的一个偏远岛屿,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18岁那年,我去伦敦读书,这是我第一次旅行。即使在那时,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我父亲很开放。 那时候,没有女孩出国。我父亲是个珠宝商,而不是像其他家庭成员那样是知识分子。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叔叔们对父亲很不高兴,因为父亲告诉他们我要去伦敦学习法律。那时候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大律师,就必须在英国学习才会受到认可。我的叔叔们很不舒服,因为我哥哥去印度上大学,我却要去英国。他们说,为什么要送女儿到英国、投资这么多钱?她以后反正要嫁人的。”

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年幼时,帕腾是个害羞的孩子,总是生活在哥哥姐姐的影子下面,而父亲总是给她很多鼓励。
帕腾:“我之所以幸运,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父亲,他确保他的四个女儿不会受歧视。我来自一个六口之家,我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我父亲强调,没有人可以歧视他的女儿。他是一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我遇见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 我现在会回想起一些小事,比如有人说我的兄弟是我父亲的金子,父亲就会说,我的女儿是我的钻石。他永远要纠正人们说的那些无聊的话。”
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帕滕回到了毛里求斯,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但是很快,她的兴趣就转向了妇女和儿童权益。
帕腾:“我有很多案子,非常忙。我也参加了政治活动并当选,我被任命为副市长。在毛里求斯,直到1980年,妇女与未成年人或残障人士的地位类似,没有丈夫的许可,她们就不能有护照,不能有银行帐户。根据法律规定,你必须服从丈夫的规定,而且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1982年大选前,法律被修改了。但是,女性并不知道。我要在离婚案件中上法庭,但是你不会看到妇女为自己的孩子而战,甚至不会为离婚而战。妇女没有任何代表,离婚是缺席宣告。孩子被判给丈夫,也没有赡养费之类的。这令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开始在选区中与妇女交谈,我发现不仅是她们不了解法律,而且她们也不知道这部法律是适用于她们的。我因此意识到我必须从这里着手,教会她们怎么用法律来促进自己的社会、经济、公民和政治权利。我去找了妇女、儿童和家庭发展部长,我告诉她,我是一个年轻律师,我想帮忙。她很欣然接受了。我说,让我们在全国搞一个 “了解你的权利运动”。她同意了。后来,政府任命我担任两个特别工作组的主席。我意识到政府甚至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我游说他们批准这部公约。然后他们又让我负责研究所有针对妇女的歧视性法律并提出建议,并且研究有关儿童的法律,以确保政府批准的法律与《儿童权利公约》保持一致。”
帕腾后来还代表毛里求斯成为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成员,其间处理过很多问题,包括墨西哥大量的杀害妇女案件,吉尔吉斯斯坦的绑架新娘问题,以及秘鲁的强奸受害者怀孕后无法得到人工流产服务等等。
2017年4月,帕滕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

帕腾:“审视自远古以来世界各地的冲突历史,在每一场战争中,在每一次冲突中,性暴力都被用作战争策略。冲突中的性暴力是最大的历史对之保持缄默的问题之一,这种罪行是最少被报道和最不被谴责的罪行。因此,实际上是在2008年安理会的第1820号决议中,世界第一次承认,冲突中的性暴力在被用作策略时会加剧冲突,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是第一次将性暴力问题纳入和平与安全政策,也是安理会第一次通过那些其身躯被当作战场的一部分的妇女和女孩的眼光来审视战争与冲突。在1994年卢旺达持续了100天的种族灭绝罪行中,有20万至50万名妇女被强奸。利比里亚内战期间有4万多妇女被强奸,在塞拉利昂有超过6万,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超过6万。我们谈论的是这样的数字。”
帕腾表示,在武装冲突中,强奸被用作一种策略,以羞辱、控制、散布恐惧并驱逐人口。当妇女和儿童遭到强奸时,整个村庄的人就会离开。 在缅甸,强奸和轮奸被作为种族清洗的手段之一,以驱逐居住在若开邦的罗兴亚穆斯林。这场种族清洗在2017年以来导致了70多万罗兴亚人逃到了孟加拉国的考克斯巴扎尔地区。

帕腾:“2017年,我到考克斯巴扎尔走访罗兴亚人。我去了不同的营地,罗兴亚人遭受的性暴力的残酷性是难以想象的。每个人都在说轮奸,提到的次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问翻译,你知道强奸这个词吗、然后才是轮奸?她说,如果她们说她们被10个人、10士兵强奸了,你想让我用哪个词呢?我才确信她知道她在说什么。这些妇女的经历都与轮奸有关,都是在丈夫面前、邻居面前、在公共场所发生。她们的遭遇类似,被绑在岩石上、树木上,被多名士兵强奸。她们年幼的女儿在屋里被强奸的同时,她们不得不赤裸裸地躺在村子里的公共地带等待被强奸,而女儿还在里面的屋子被烧毁了。那时是十一月份,还很热,她们抱着婴儿。我们问他们,婴儿还好吗?她们说,我们和孩子在一起是很幸运的,因为她们看到很多婴儿被扔进火里。然后她们开始哭泣。她们说, 2017年那一年里,她们都无法开着门睡觉,因为军人会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过来,如果有一个新生婴儿,他们就会把婴儿扔到村里的水井里。水井里有了尸体,他们就没有水喝了。那天,前来与我交谈的有500名妇女……我转过身来。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翻译,每一个人都在流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了想,然后我说,让我们祈祷吧。我不知道从那里来的这个念头。人们本来在尖叫,哭泣,这时她们都平静了下来。我说,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我们祈祷了大约30分钟,房间里完全安静了下来……当时我穿着印度的莎丽,我后来把这些裙子干洗了带了回来。我再也没有穿这些裙子。 我不能穿。太痛苦了。因为我从那个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女人都在哭,我的裙子湿透了。我会打开衣柜,看着这些裙子,这让我想起这些幸存者。她们是我道德的指南针,我必须继续为她们而战。 这就是让我前进的动力。”
帕腾2017年6月上任后的第一次实地访问是前往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首府迈杜古里。尼日利亚东北部长期遭受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哈拉姆暴行的肆虐。该组织不断袭击平民,绑架妇女和女孩充当性奴隶。
帕腾:“我看到了被博科哈拉姆释放的这些年轻女孩。我称她们为女孩,是因为她们的年龄不超过十二、三岁,而且她们的膝上都有小婴儿。在与她们的交谈中,我意识到她们获释后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在营地里,她们因为生下了博科哈拉姆的婴儿而蒙受污名。当我同几个女孩交谈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们说,你知道,和所谓的博科哈拉姆丈夫在一起我们过得更好一点。我们被迫嫁给他们。我们怀孕了。那的确是强迫婚姻,强迫怀孕,但我们并没有像在镇上那样每天受到虐待。我们去取水都会被营地里的男人和女人虐待。这是我关于受辱问题的第一课,这种耻辱不仅涉及母亲,而且涉及孩子。我在会见尼日利亚当局的时候说,这些婴儿是什么状况?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国籍。他们将变得激进化。我意识到针对强奸出生的儿童存在巨大的政策空白,甚至《儿童权利公约》也没有规定。我与公约的执行机构儿童权利委员会签署了合作框架,我说,你们从未对那些无国籍的因强奸而出生的孩子做过任何工作? 2019年,我第一次促使安理会通过决议,其中认可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应享有权利。那次访问中,后来我从尼日利亚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到了那些遭受强奸的妇女因被排斥而蒙受痛苦的真相。这些女人中的大多数遭到了配偶、家庭和社区的排斥,就像尼日利亚的那些年轻女孩一样。强奸的确是一种最少受到谴责的犯罪,肇事者被遮掩,而污名却落在了受害者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办公室在将污名转移回肇事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原因。

帕腾作为特别代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让冲突中性暴力受害的声音被听到。她的办公室目前正在制作一本电子书,《幸存者的声音》。幸存者希望世界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世界应该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在2014年到2017年的接近3年半时间里,极端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大片领土,并且在北部绑架了众多少数族裔雅兹迪妇女和女孩。
帕腾:“每个实地访问都令人心碎。一个故事比另一个故事更令人伤心。但是我在摩苏尔第一次遇到雅兹迪妇女时,目睹了格外的创伤,我面前的妇女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心理医生告诉我,这些妇女中有许多是几个月前被释放的。她们被释放时处于半昏迷状态。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医疗或社会心理支持。有时营地里会有医疗服务,但她们不敢去,由于害怕被逮捕,她们被吓得聚在一起相互支持。她们因为与伊黎伊斯兰国的人员一起生活了三、四年有可能会被审讯。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现实。她们沦为性奴,一般的雅兹迪女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被卖了无数次,每天被强奸20次以上。她们像那样生活了三到四年。”
幸存的雅兹迪妇女难以回归社区。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往往会被视为与伊黎伊斯兰国有牵连的人而遭到排斥。

帕腾:“我的前任实际上与已故雅兹迪精神领袖巴巴谢赫(Baba Sheikh)举行了会见,在影响巴巴谢赫接受这些妇女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接纳了这些妇女,她们回来了,但是当我去的时候,我听到了她们痛苦的故事。很多人没有回来,因为她们不想把孩子抛在后面。根据法律,如果父母双方均为雅兹迪人,那么孩子被视为雅兹迪;一个父亲不详的孩子会被认为是穆斯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修改法律,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目前为止,这些孩子还分散在不同的孤儿院中。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甚至没有国籍。伊拉克在不到一个月前颁布了一项法律,为雅兹迪社区和其他社区提供赔偿、教育、就业等。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关于儿童的任何内容。”
在非洲最新的地区冲突——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2020年11月爆发的冲突中,仅根据目前能获得的有限信息,人们也得知其间存在着大量的性暴力行为。
帕腾:“我有一段提格雷一家医疗机构进行的手术视频。一名医生从一名年轻女子的身上去除了两个指甲。这个女孩在十天的时间里被当作性奴隶,被多次强奸,最终,她逃脱来到了医院。医生从她身上去除了两个指甲。然后,我摘下了眼镜,因为我不想再看了。医生还去除了另外几个异物。我无法入睡。我告诉了我的工作人员这段视频,但是我说我不会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不会删除它。这就是女人的经历。她们的身体成为了战场。现在,我的工作是推进这项任务,重点放在预防上。我们总在谈论预防和应对。但实际上,我们最终做出了更多回应。我正在制定预防框架。每次遇见幸存者时,我总是问,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些事情?答案你会很惊讶。我记得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位母亲告诉我,当我去森林里取水的时候,我四岁和八岁的女儿被强奸了。如果她们在学校,就不会被强奸。当我与苏丹或索马里的妇女交谈时,她们说,我们必须走路去取水。如果村子里有水,我们就不必在偏远的地方走这么长的路。在南苏丹的朱巴,妇女们告诉我,外出时,我们总是会被强奸。我就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我说,但是,为什么你要出去收集柴火?男人们为什么不去?她们很沮丧。她们说,请跟我来。你想看看男人在哪里吗?那边有一块墓地。男人们就在那里。他们被杀了。我们只会被强奸。”
帕腾表示,对她而言,如果没有正义和问责,就谈不上预防,与冲突中的性暴力作斗争就是与普遍的有罪不罚做斗争。
帕腾:“的确,正义是罕见的例外,有罪不罚是规则。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向犯罪者和可能的犯罪者发出强烈的信号,强奸一个女人,一个女孩,一个男人或一个男孩不会没有代价,我们会制裁你。当你与雅兹迪妇女交谈时,她们会告诉你,除了支持服务之外,她们还希望获得正义和赔偿。无论是在伊拉克,尼日利亚,还是在苏丹,索马里,她们都告诉我,她们想有一天在法庭上伸张正义。对我而言,到目前为止,令人非常沮丧的是,在性暴力被用作恐怖主义手段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博科哈拉姆或伊斯兰国的人因性暴力而受到起诉。他们正在根据反恐法受到起诉,但不是因为性暴力。这很无奈。因此,我一直在与这些国家的当局沟通。在伊拉克,司法委员会主任告诉我,对我们来说,证明与极端团体的隶属关系并判罪更容易,而且我们会判处死刑。所以对他来说,事情很简单。我告诉他,那你将不会有历史记录女性的经历。”
帕腾说,特别代表这个职位对她而言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项使命,她要让冲突中的性暴力可以预防,会被惩罚,她要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去支持幸存者的生活。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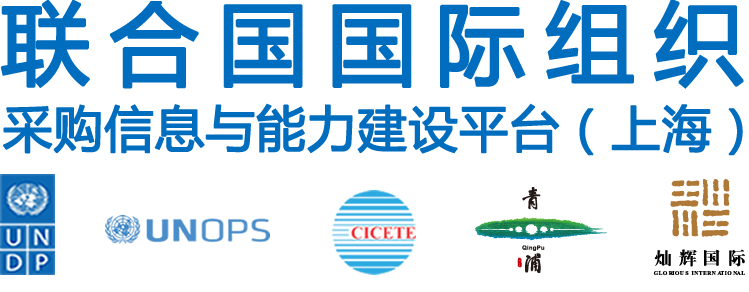
 首 页
首 页 关于项目
关于项目 采购信息
采购信息 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配套服务
配套服务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448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802004489号